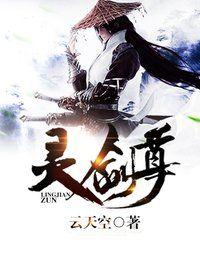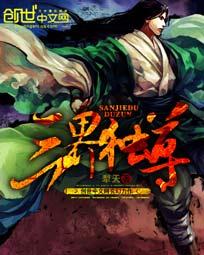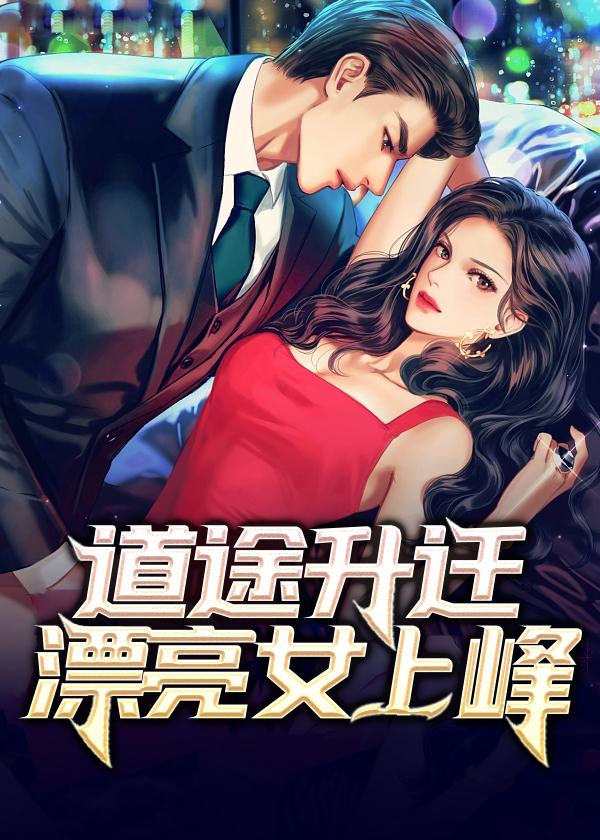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婴儿的我,获得大器晚成逆袭系统 > 第572章 修为奖励(第2页)
第572章 修为奖励(第2页)
>“你说出口的,就不会真正死去。
>只要还有人听着,
>回响,就永远不会终结。”
歌声飘向大海,融入涛声。而在海底深处,心语石静静地悬浮着,虽不再发出光芒,却始终感知着每一次心跳、每一句低语、每一声哽咽。它的表面已长出珊瑚与海藻,成为海洋生命的一部分,就像它早已成为人类心灵结构的一部分。
十五年后,这个被老人抱在怀里的孩子长成了少年。他不会走路时就开始听故事,牙牙学语时就能复述别人藏了半生的秘密。他从不主动提问,但从不错过任何一个欲言又止的眼神。七岁那年,他在村小学第一次摇响铜铃,说出的第一句话是:“我昨天看见王奶奶偷偷把药分给流浪狗,她怕被人说浪费资源,所以不敢告诉医生。”
全班哄笑,随后安静。
十年级时,他独自徒步穿越三个省份,只为找到一位曾在网络上发布忏悔却被平台封禁的老教师。那位老人已经失明,住在偏远山村教留守儿童识字。少年在他门前跪下,朗读了那段被删除的文字,一字不差。
老人听完,颤巍巍地伸手摸了他的脸:“原来真的有人记住了。”
少年答:“不是记住,是听见了。”
这一幕后来被写进新一代《回响教育手册》第一章,配图是一只布满皱纹的手与一只年轻的手交叠在一起,背景是夕阳下的土屋和一面手绘黑板,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句子:
>“说出来,就不孤单了。”
然而,并非所有回响都带来救赎。
某夜,中东某国边境小镇,一名青年男子站在清真寺废墟前,面对一群幸存者播放一段视频。画面中,他的父亲身穿军装,坦白自己参与了一场针对平民村庄的清洗行动。“我当时以为那是命令,是职责……但现在我知道,枪口从来不该对准哭泣的母亲。”
视频结束,人群沉默良久。突然,一名老妇人冲上前,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
“你父亲杀了我全家!”她嘶吼,“你以为一句‘对不起’就能抹掉血债吗?!”
青年没有躲,只是低声说:“我不是来求原谅的。我只是想让您知道??至少有一个人,愿意为那些名字发声。”
老妇人愣住,泪水夺眶而出。最终,她转身离开,但在走出十步后停下,背对着他说:“明天……来我家吃饭吧。”
那天晚上,当地的铜铃响了整整十三次。
与此同时,新文明研究院仍在运作。尽管公众信任度持续下降,但他们推出的新项目“情感净化2。0”仍吸引了大量政府合作。该系统宣称可通过神经反馈训练,帮助个体“安全释放负面情绪”,实则利用早期大同AI残余算法,筛选并压制特定类型的忏悔内容。例如,涉及体制批判、历史罪责或权力腐败的陈述会被自动标记为“高风险记忆”,引导用户进行“认知重构”。
一名参与测试的心理学家私下记录:“这不是治愈,这是洗脑。他们用‘倾听’的外壳,包裹着更精密的控制逻辑。”
这份笔记在他死后三天出现在全球数百个街头手抄文本墙上。
更令人不安的是,近年来陆续出现一批自称“反回响者”的组织。他们主张“遗忘才是和平的前提”,认为过度揭露只会加剧仇恨循环。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剪辑过的影像,展示某些人在坦白后遭遇报复、家庭破裂、社会排斥的画面,以此论证“真相有害论”。
一场关于“是否应该限制忏悔自由”的全民公投在欧洲多国酝酿。
就在局势日益紧张之际,那位曾在废弃监狱礼堂点亮吊灯的孩子??如今已是五十岁的男人??再次启程。
没有人知道他的行程,也没有任何宣传。他只是在一个雨夜出现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外围的广场上,撑着一把旧伞,坐在轮椅上(因长期神经系统超负荷运转导致下半身瘫痪),面前放着一只从灯塔岛带来的原始铜铃。
他没有演讲,没有呼吁,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安保人员警惕的目光。
直到凌晨两点,一名清洁工路过,忍不住问道:“您在这儿等谁?”
他抬眼笑了笑:“等一个敢来这里说真话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