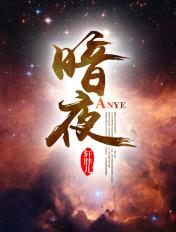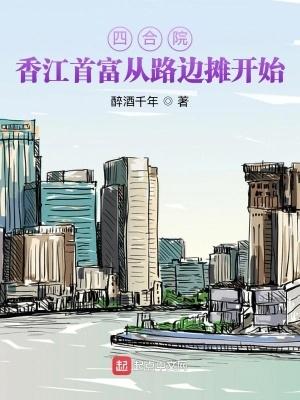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权臣西门庆,篡位在红楼 > 第148章 官家追师师大官人画师师(第1页)
第148章 官家追师师大官人画师师(第1页)
蔡京回到他那气派非凡的相府,朱漆大门“哐当”一声在身后闭了个严实,外头的车马喧嚷是隔断了,可心窝子里那团疑云,却像六月天的闷雷,越滚越浓,堵得他心口发慌。
他挥苍蝇似的把跟前伺候的都撵了个干净,独个儿踅进那静得落针可闻的书斋。
连头上那顶千斤重的太师官帽都忘了摘,便一屁股瘫在紫檀木太师椅里,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。
“邪道…邪道…”他嘴里头嚼着这两个字,如同嚼着块没滋味的蜡。眉头锁得死紧,能夹死个苍蝇,那保养得宜的手指头,焦躁地敲着光溜溜的桌面,笃笃笃,敲得人心烦意乱。
今日朝堂之上,官家那番关于“新派画技”的论断,言犹在耳,掷地有声,下了定论。
这种画技只可存于市井坊间,供贩夫走卒猎奇,断不可登大雅之堂,更不得入翰林图画院!”
这番话,斩钉截铁,毫无转圜余地。
蔡京作为宰相,自然心领神会。
然而!
就在这雷霆万钧的论断之后,官家为那好像在哪听过的画师亲赐了前所未有的恩典!
“官家这唱的是哪一出?”蔡京只觉得脑仁子像被滚油煎着,太阳穴“突突”地跳,活像里头藏了只蛤蟆。
他端起手边那盏早凉透了的定窑白瓷茶盏,送到嘴边,又重重撂下,哪还有心思品这茶?
这事儿,透着邪性!
蔡京自诩是揣摩圣意的祖宗,三朝元老,几十年的道行,什么风浪没见过?可今日官家这手,真真叫他“丈二的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”。
那画儿难道是狐狸精画的?能把官家的魂儿都勾了去?让这素来讲究风雅、推崇正统丹青的官家,竟连自家的金口玉言、朝廷的体面规矩都顾不得了,活生生打了自家的脸面?
岂止是他蔡京想破了头!
此刻,整个东京汴梁城的文武官老爷们,心里头都像揣了二十五只耗子——百爪挠心!
宫门一落钥,那些个刚下朝的文武大臣,一个个脸上都挂着“想不通”三个大字。平日里为点鸡毛蒜皮争得面红脖子粗的冤家对头,这会儿倒出奇地齐了心,三三两两凑在一处,交头接耳,咬耳朵根子:
“啧!怪事年年有,今年特别多!官家这葫芦里卖的,莫不是迷魂汤?”一个老学究捻着山羊胡,摇头晃脑。
“谁说不是呢!前脚刚把那画技贬得一文不值,踩进了泥里;后脚就把献画的商贾捧到了云彩眼里!显谟阁直阁啊!多少正经科举出身的清流熬白了头也摸不着边!”另一个酸溜溜地附和。
“那清河县的西门庆,该叫西门显谟了,真真是祖坟冒了青烟,走了狗屎运,撞上了真佛?”
“君心似海,深不可测啊……”蔡京长长吐出一口浊气,仿佛要把胸中的郁闷都吐出来。
他睁开那双精光四射的老眼,里头却还是蒙着一层化不开的迷茫。他这双眼睛,看透了多少人心鬼蜮,算尽了多少朝堂风云?如今竟莫名的给难住了!
这西门庆到底是谁,越听越耳熟!
西门大官人不知道,此后这半月来,蔡京是食不甘味,夜不安寝,心里头那杆秤拨来拨去,怎么也拨不平。
生生熬得人瘦了一圈,眼窝子都抠了进去,下巴颏也尖了,连那身紫袍穿在身上都显得空荡荡的。真真是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,算天算地,算不透官家这一份谁也猜不着的心思!
大内御书房里,明晃晃的烛火点得如同白昼,将满室紫檀木的沉郁光泽和上等徽墨的清苦香气都照得纤毫毕现。
可这通明的光亮,非但没驱散那股子浸透骨髓的冷清孤寂,反将那空落落的人影儿,在雕花窗棂上拖得老长,更显得形单影只。
官家赵佶,今夜既没心思去碰那堆积如山的奏章——那些劳什子,看着就让人脑仁疼。
也没兴致提笔挥洒他那冠绝天下的“瘦金体”。
他只是一个人,像个丢了魂的痴人,呆坐在那冰凉的紫檀御案后头。案上,别无他物,只摊开着一幅新裱好的画儿。
一边是勾魂摄魄的美人,一边是嶙峋冷硬的怪石。
可官家那双惯于鉴赏天下珍玩的眼,此刻只死死钉在那画中人的身上,哪还容得下半点顽石的影子?
他伸出手指,此刻却带着一种近乎朝圣的、难以抑制的轻颤,一遍,又一遍地,小心翼翼地抚过那画中人的眉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