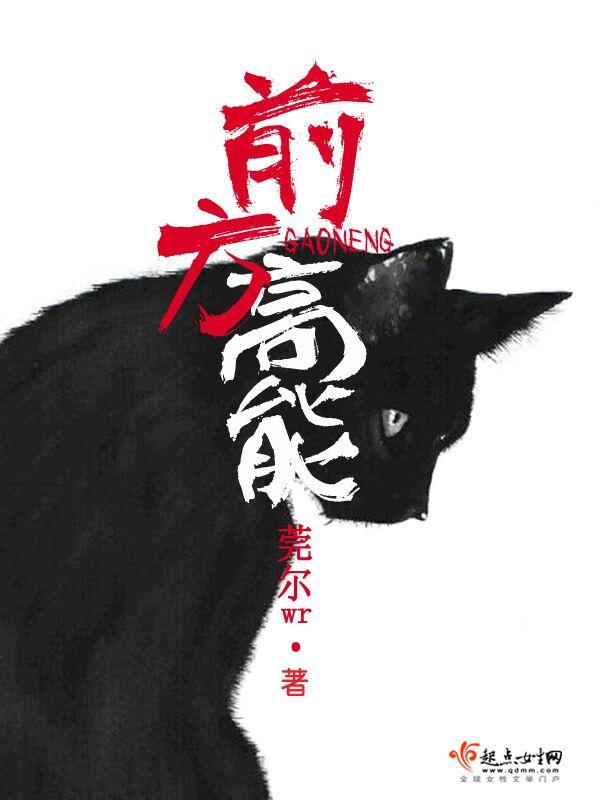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沧澜之下 > 第 80 章(第2页)
第 80 章(第2页)
“未必是针对我们,但时机太巧。”云青走到窗边,撩起帘角向下看了一眼,“我还去了两家消息灵通的茶楼,听说近半月,码头来了几拨生面孔,不像是正经商贾,常在码头和客栈附近转悠,打听南下的船客,尤其是……带有女眷、或有伤病在身的。”
阿洙的手微微收紧。果然。
“老陈头那边呢?”她问。
“他打听到,明日午后有一班‘顺风号’货船南下,经叙州、宜宾,直放滇东曲靖。船主是个老江湖,只要钱给够,不问客人来历,也肯搭载散客。”云青转身,“我们乘船。水路虽慢,但比陆路隐蔽,也免你脚伤再受颠簸。”
“好。”阿洙没有异议。
傍晚时分,老陈头带着新买的衣物回来。云青挑了一套靛青细布长衫,阿洙则是一身藕荷色绣缠枝纹的衣裙,料子中等,样式是蜀中流行的款式,不算打眼,却比之前的粗布衣衫体面许多。
入夜,两人下楼用饭。客栈大堂热闹非凡,划拳行令声、谈笑吆喝声不绝于耳。云青选了个角落的桌子,背靠墙壁,视野开阔。
饭菜上桌,皆是蜀地风味,麻辣鲜香。阿洙吃了两口,便被辣得咳嗽,眼泪都出来了。云青默默将一碗清淡的豆腐汤推到她面前。
正吃着,邻桌几个商人打扮的汉子高声谈论起来。
“……听说没有?滇南那边近来不太平!好几个寨子都传闹‘水鬼’,牲口被拖走,夜里还能听见哭嚎!”
“嗨,什么水鬼,八成是山里那些不服王化的蛮子又闹事了!朝廷这两年对西南用兵,那些土司心里能痛快?”
“不止呢!我有个表亲在滇东跑马帮,说前些日子,澜沧江有一段忽然断了流,露出河床,里头全是白骨!吓得当地人都不敢靠近,说是‘河神发怒’!”
“澜沧江?”另一人插嘴,“那可是通往滇西缅地的要道!这要真出了邪乎事,商路可就断了!”
阿洙手中的汤匙顿住了。澜沧江……白骨……河神发怒?她与云青交换了一个眼神。
云青神色不动,仿佛只是随意听着,夹了一筷子菜。
这时,客栈门口又进来一行人。为首的是个锦衣华服的中年人,面色白净,眼神精明,身后跟着几个随从,看着像是大户人家的管事。他一进来,目光便在大堂内扫视一圈,最后在柜台前停下,与掌柜低声交谈起来。
云青的背脊几不可察地绷直了一瞬。
阿洙顺着他的目光看去。那中年人……似乎有些眼熟?她仔细回想,忽然想起,在京城司天监藏书楼那日,楼下搜查的太监里,仿佛有个声音与这人略有相似?不,不对,不是太监。但那种刻意压低却仍显尖细的嗓音,和眉眼间那股子阴柔的精明气……
那人似乎察觉到了注视,目光朝这边扫来。云青适时低头,为阿洙舀了一勺汤,语气自然:“尝尝这个,不辣。”
阿洙会意,也垂下头,小口喝汤。
那人的目光在他们这桌停留片刻,似乎未发现异常,又转开了,继续与掌柜说话。不多时,便带着随从上了楼。
“那人……”待他们身影消失,阿洙才极低声问。
“宫里的。”云青放下筷子,声音压得只剩气音,“虽然换了便服,但走路的姿势、看人的眼神,是内廷里浸淫久了才有的。”他眼底寒意凝聚,“看来,有人不仅派了江湖眼线,连宫里得力的人都放出来了。对西南之事,是志在必得。”
阿洙的心沉了下去。连宫中内侍都亲自出马,可见二皇子或皇帝对“水魄”之事重视到了何等地步。他们的前路,越发凶险了。
“明日船期,未必太平。”云青看着她,“但我们必须走。留在泸州,迟早会被翻出来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阿洙点头,眼中并无惧色,“那就闯过去。”
云青凝视她片刻,点了点头,不再多言。
夜色渐深,客栈大堂依旧喧哗。但角落里这一桌的两人,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寂静而紧绷的世界。窗外,泸水汤汤,奔流不息,载着满河的月光与看不透的迷雾,向着更南的、危机四伏的群山深处流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