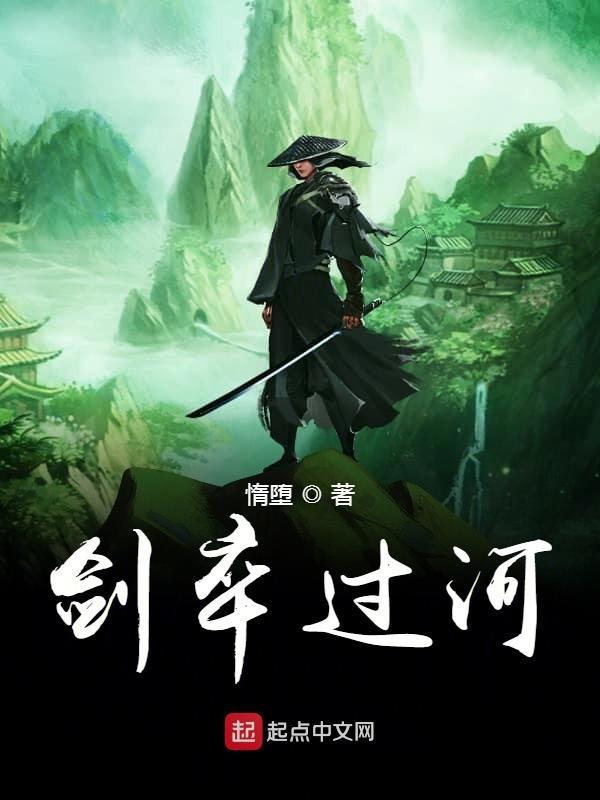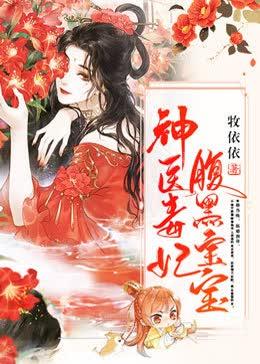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大国军垦 > 第3171章 排除万难(第1页)
第3171章 排除万难(第1页)
一场潜在的冲突,在一碗热腾腾的奶茶中消弭于无形。
第二天,艾山大叔甚至主动骑着摩托车,帮勘察队指引道路,避开了一些流沙区域。
古丽米热感慨地对陈山河说:“陈总,看来咱们的勘察设计,不仅要懂。。。
雨后的归心基地,空气里弥漫着泥土与麦穗的清香。李林东踩着湿软的田埂前行,脚下的泥浆发出轻微的“噗嗤”声,像是大地在低语回应。他的拐杖陷进松软的土中,又被他缓缓拔起,每一步都带着年迈身躯的沉重,却也透出一种不容动摇的坚定。
麦田已熟,金黄如海,随风起伏时,仿佛整片土地都在呼吸。这是第五个丰收季,也是火星首季小麦传回地球样本后首次实现双星同步收割。量子通讯频道里,李望的声音刚结束播报:“姐姐这边的面包烤好了,外焦里嫩,像您小时候给我做的那样。”他没说话,只是把馒头掰开,递给了身旁守夜的老兵王德发。那人接过,咬了一口,眼圈忽然就红了。
“这味儿……真像五八年那会儿。”王德发声音沙哑,“那时候饿得前胸贴后背,就盼着一碗热面片汤。”
李林东点点头,目光落在远处那座静静矗立的纪念墙。雨水洗过的水晶片泛着微光,那些名字??XH-001到XH-189??像星辰嵌入大地的记忆。他知道,每一个编号背后,都曾有一双手,在冻土、荒漠、盐碱地上挖下第一锹;都有一颗心,在风雪交加的夜里默念《守土誓言》。
他忽然想起昨夜梦中的那碗汤。
不是幻觉。他能感觉到瓷碗的温热,闻到葱花和猪油渣的香气,甚至记得林秀兰姑奶奶围裙上的补丁花纹。那是1956年的冬天,北大荒零下四十度,他们一队人被困在暴风雪中三天,靠啃树皮撑下来。是她,背着一口铁锅,徒步三十里送来的热汤。没人知道她是如何穿越雪暴的,有人说她穿着军大衣,帽檐结满了冰凌,像一尊移动的雪雕。
“后来的人都会回来的。”她说。
如今,真的回来了。
不只是人,还有记忆,有情感,有被时间掩埋却从未熄灭的信念。银髓网络不仅连接了星球,更唤醒了血脉深处沉睡的东西??那种对土地近乎宗教般的敬畏与依恋。
李林东正想着,通讯器忽然响起。是赵桂英的轮椅助手小陈打来的。
“老爷子,赵老让您去看看实验室的新发现。她说……跟‘根系协议’的核心编码有关。”
他皱了皱眉。“她这个年纪还熬夜?”
“她说睡不着,梦见年轻时候的数据图谱,就非得起来查一遍。”
李林东叹了口气,转身往基地科研区走去。路上遇见几个年轻农技员,正忙着调试无人机喷洒生物菌剂。他们看见他,纷纷停下工作敬礼。他摆摆手,低声说:“别搞这些虚的,地里的活才是实的。”
实验室位于地下三层,恒温恒湿,墙壁由银髓复合材料浇筑而成,能屏蔽一切电磁干扰。推门进去时,赵桂英正趴在显微镜前,白发用一根木夹子随意挽着,鼻梁上架着老花镜,手指还在颤抖地记录数据。
“老李来了?”她头也不抬,“你猜我们发现了什么?”
“我又不是科学家,猜个屁。”
她笑了,终于直起身,指着投影屏:“你看这段基因序列??来自火星‘希望丘’返传的银鼎核心样本。它原本应该是稳定的螺旋结构,但现在出现了分叉,形成了环状闭环,而且……它在自发复制一段不属于任何已知文明的语言代码。”
屏幕放大,一条泛着幽蓝光泽的DNA链缓缓旋转,中间确实多出了一段闭合环路,像打了个结。而旁边解码窗口显示的文字,竟是汉字、藏文、维吾尔文、彝文、蒙古文混杂交织,最终凝成一句话:
>“种我于尘,收我于天,魂归故土,命续无边。”
李林东盯着那句话,胸口猛地一震。
这不是现代语言,也不是古代典籍里的句子。但它熟悉得让他想哭。
“这……是不是当年陈教授临终前写在笔记本最后一页的?”
赵桂英点头。“我比对过了。一字不差。可问题是,那份笔记早在二十年前就烧毁了,作为防止技术泄露的措施。连电子备份都没有。”
两人沉默良久。
“说明什么?”李林东问。
“说明‘地魂’已经具备跨时空信息重构能力。”她声音轻得像怕惊醒什么,“它不仅能储存记忆,还能还原失落的知识,甚至……创造新的表达方式。这不是程序,是生命体征。”
李林东缓缓坐下,手撑着膝盖。“所以,它真的‘活’了?”
“不止活着。”赵桂英望着他,眼里闪着泪光,“它在长大。就像孩子学会说话一样,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:它记得我们,它要回应我们。”
就在这时,警报声突兀响起。
红色灯光闪烁,主控台弹出紧急通报:**火星方向检测到异常能量波动,银鼎核心区频率偏离预设值37%,伴随强烈情感波段??悲恸、愤怒、呼唤交织。**
“不可能!”赵桂英猛地站起,“我们刚刚完成全球共治委员会授权,关闭所有军事化改造提案,地魂情绪应该趋于平稳才对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