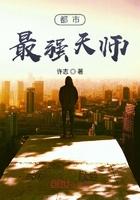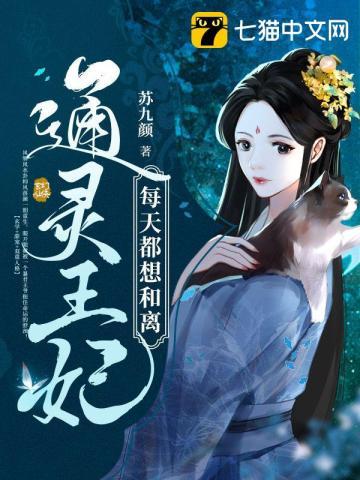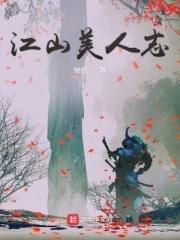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非正常美食文 > 第512章 土豆饺子(第2页)
第512章 土豆饺子(第2页)
第三个是个网红博主,戴着口罩,不敢报真名。她掏出手机,播放一段直播回放:画面中,她对着镜头哭诉童年被家暴的经历,弹幕却刷着“演得不错”“打赏666”。她说:“我编了百分之七十。但那百分之三十的真,却被当成表演。”
林小满让他们都进来了。
他让王素芬煮了一大锅白粥,不加料,也不调味。每人一碗,坐下喝。
“在这里,”他说,“没人评判你说了多少真话。只问你??敢不敢从这一刻开始,少说一句谎。”
那位母亲哭了。她说,其实孩子死后,她每天晚上都穿着他的校服睡觉,怕忘了他的味道。
老师低头搓着手:“我以前总说‘正能量作文才能得高分’。现在我才明白,逼人伪装,就是在杀人。”
博主摘下口罩,露出一张浮肿的脸:“我想重新发一条视频。标题就叫《我不是受害者专业户,我只是个受伤的人》。”
林小满点头:“那就在这儿录。用李哲的录音机,不剪辑,不美颜。”
中午,苏慧带着打印好的《家属证言》去了周小宇的学校。她在公告栏贴完转身时,看见几个学生站在远处看着她。其中一个女生走上前,低声问:“我能抄一份吗?我也……有个朋友去年跳了。”
苏慧把原件给了她:“拿去吧。顺便告诉你们老师,下周我会去开讲座,题目是《如何听懂孩子的‘反话’》。”
下午三点,社区礼堂。
“晚风呢喃”的线下分享会准时开始。现场坐了近百人,大多是年轻人,手里拿着笔记本或手机。当主播走上台时,全场安静。
她没化妆,也没戴耳饰,只穿一件洗旧的卫衣。
“我叫林晚。”她说,“过去五年,我讲了上百个情感故事。有被婆婆逼疯的儿媳,有替弟弟还债二十年的姐姐,有在雨夜抱着骨灰盒跳舞的母亲……可这些,全是假的。”
台下一片哗然。
“我没有婆婆,没弟弟,母亲健在。”她声音平静,“但我发现,只要故事够惨,就有人愿意相信,愿意打赏,愿意转发。于是我就编下去了。直到看到《云边书》的评语??‘它不提供答案,只记录提问的人’。我才意识到,我一直在消灭提问的人。”
她从包里拿出一叠信:“这些都是读者写给我的。有人说,听了我的故事,终于敢告诉父母自己被性侵;有人说,因为我的‘经历’,鼓起勇气去做心理咨询。可我现在必须告诉他们:对不起,我是骗子。”
有人站起来质问:“那你是不是也在消费真实苦难?”
她点头:“是。而且我比那些无意中伤害别人的人更恶劣??因为我明知故犯。”
但她接着说:“但我今天来的目的,不是求原谅。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件事:把这些虚构的故事,重写一遍,换成真实的版本。比如,把‘婆婆逼我流产’改成‘我和男友因经济压力选择分手’;把‘为弟还债二十年’改成‘我因讨好型人格长期被家人索取’。”
她顿了顿:“虚假的故事能打动人心,说明我们渴望真实。那为什么不直接给真实一个舞台?”
会场陷入长久沉默。
然后,一个女孩举手:“我可以分享我的真实吗?不是为了流量,就……就想让人知道,我不是装病逃课。”
另一个男生说:“我也想讲。我爸酗酒,我妈离家出走,我每天回家要看妹妹写作业,还要做饭。我没空参加社团,不是不合群,是我真的累。”
林小满坐在后排,默默听着。结束后,他走上前,递给她一张纸条:
>虚构不可怕,可怕的是真假不分。
>从今往后,你的直播间叫《补真计划》。
>每一场,都用来修正过去的一句谎。
她接过纸条,泪流满面。
同一时间,林溪正在家里重写她的获奖作文。
原题是《山间少年》,描写自己如何在山村支教的父亲影响下,立志改变贫困教育。如今她撕掉全文,写下新标题:
>《便利店里的时间》
开头第一句是:“我爸在24小时便利店值夜班,从我六岁起,他就没见过我早上起床的样子。”
她写他冬天冻裂的手指,写他偷偷把顾客丢弃的蛋糕带回家当晚餐,写他每次看见新闻里“留守儿童自杀”时,都会默默抽烟到凌晨。
她写完最后一句:“我不是要博同情。我只是想说,我的深度不在远方,而在每个不敢说累的夜晚。”
她点了提交,署名:林溪,真实作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