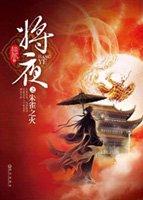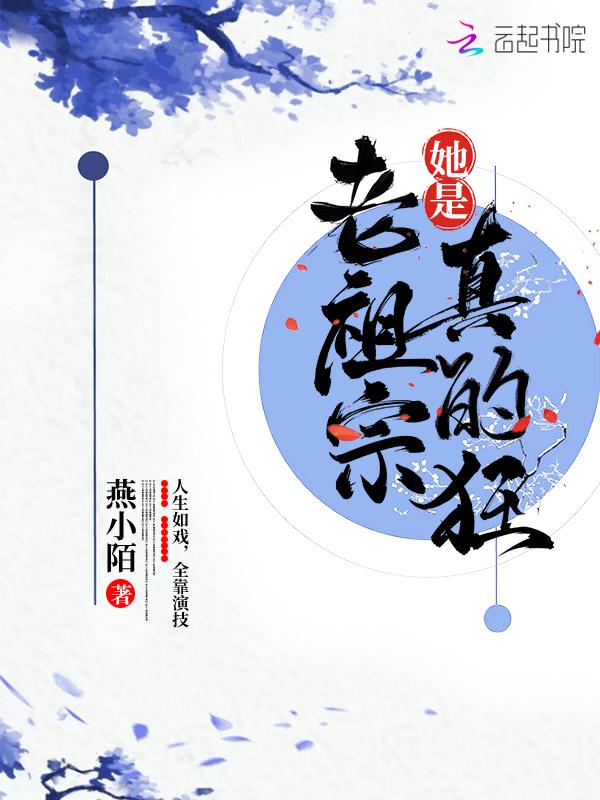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这个明星不想再卷了 > 第二百七十九章 这就是口碑(第2页)
第二百七十九章 这就是口碑(第2页)
而火焰一旦燃起,就不会轻易熄灭。
三天后,林知梦和苏超如期抵达北京。三人约在学校旁边的小茶馆见面。窗外下着细雨,屋檐滴水声清脆悦耳。林知梦穿着素色棉麻长裙,背着一个旧帆布包,里面塞满了教案和学生习作复印件;苏超则一身运动装,脚踩球鞋,看起来随时准备跳支舞。
“你这状态不错啊。”王劲松打量着他,“不像个退休艺人,倒像个体育老师。”
“本来就是。”苏超咧嘴一笑,“我现在每周去三所小学教舞蹈课,孩子们叫我‘超哥’。有个一年级的小胖子跟我说:‘老师,我跳不好,但我喜欢动。’我说,那就对了,跳舞不是为了好看,是为了快乐。”
林知梦接过话:“所以我才想办这个写作营。城市里的孩子有太多表达渠道,可那些随父母漂泊的孩子呢?他们没有稳定的学校,没有固定的老师,甚至连一本属于自己的作文本都没有。但他们也有梦,也会写诗,也会在日记里偷偷画星星。”
王劲松点点头:“我记得李小苗第一次交作业时写的那首诗??‘月亮是我家的灯,照亮妈妈打工的城市’。那种痛,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写得出来。”
“所以我们要做的,不是教他们怎么拿奖,而是让他们知道:你们的声音值得被听见。”林知梦目光坚定。
苏超掏出一张地图铺在桌上:“我已经联系了几位老朋友,都是曾经在娱乐圈混过、后来退出的人。有人开了农场,有人做了心理咨询师,有人专门辅导艺术生。他们都愿意加入,做志愿者导师。我们可以搞‘跨界分享会’,让孩子们看到人生的多种可能。”
王劲松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的地点,忽然觉得胸口涌起一股久违的热血。
这不是一场表演,也不是一次作秀。这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,修补这个社会被忽视的角落。
会议结束时,天已放晴。三人并肩走出茶馆,阳光洒在湿漉漉的地面上,反射出细碎的光芒。路过一所小学门口时,几个放学的孩子正围在一起读一本书。王劲松走近一看,正是《停下来的人,才是自由的》。
一个小女孩抬头看见他,惊讶地睁大眼睛:“你是……王老师?”
他蹲下身,微笑道:“是啊,你怎么认出来的?”
“书后面有你的照片!”她兴奋地说,“我还给你写了信,寄到了出版社!我说我也想当作家,但我语文成绩不好……你会回我吗?”
王劲松从包里拿出笔,在书页空白处写下一行字:“致未来的诗人:请继续写,世界需要你的声音。”然后签上名字,递还给她。
“会的。”他说,“只要你不停笔,我就一定读。”
女孩抱着书跑开,笑声如铃铛般散落在春风里。
那一瞬间,他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??那个躲在出租屋里熬夜改稿、被七次退稿仍不肯放弃的年轻人。
原来,命运真的会循环。只不过这一次,他不再是那个渴望被看见的人,而是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光。
当晚,他独自去了趟望京的一家小型剧场。那里正在上演一部由农民工子女参与创作的话剧,名字叫《爸爸的火车票》。剧情很简单:一个男孩每年只能见父亲一面,每次分别时,他都会偷偷藏起父亲留下的火车票根,贴在墙上。十年过去,那面墙变成了星空。
演出结束时,全场寂静无声,随后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。王劲松坐在角落,眼眶早已湿润。
谢幕后,导演邀请他上台交流。他接过话筒,声音有些沙哑: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部戏的艺术水准,但我知道,它是真实的。真实到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在片场哭戏NG八次时,导演骂我‘连感情都不会演’。可今天这些孩子告诉我,真正的表演,不需要技巧,只需要真心。”
台下响起热烈的回应。
他继续说道:“有人说这个时代太浮躁,没人愿意听慢故事。可我觉得,正是因为浮躁,我们才更需要这样的声音。它们或许微弱,但正因为微弱,才显得珍贵。”
回到家中已是深夜。周晓棠还没睡,正在灯下读一本儿童心理学书籍。他走过去,轻轻抱住她。
“今天看了一个话剧。”他说,“讲的是留守儿童的故事。结尾时,那个男孩对着天空喊:‘爸爸,我不是不想你,我是怕你不记得我。’”
周晓棠靠在他怀里,轻声问:“你会让望舒将来也经历这些吗?”
他摇头:“不会。我再也不会让自己成为那个缺席的父亲。”
她抬起头,眼中泛着泪光:“你知道吗?有时候我会害怕。怕你哪天又接到天价片约,怕你被掌声诱惑,怕你突然说‘我要回去试试’。”
他握住她的手,一字一句地说:“我不会再走了。不是因为我厌倦了舞台,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,最大的舞台不在聚光灯下,而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刻。陪你做饭,陪孩子学步,陪你看一场无关紧要的日落……这些才是我真正想演的角色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