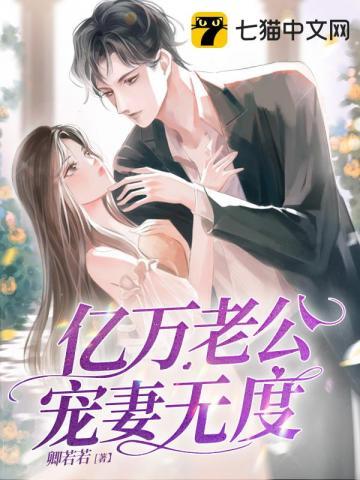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葬明1644 > 第255章 覆亡(第2页)
第255章 覆亡(第2页)
四月二十四日入夜,清兵以红夷大炮猛烈攻城,轰塌城墙,二十五日扬州城告破,总兵刘肇基战死,知府任民育、何刚等殉国。
史可法被俘之后,当面拒绝多铎的招降,也壮烈牺牲。
随即,多铎以扬州不听招降为由,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屠城。
屠城从二十五日开始,持续到五月初一,除少数提前出城以及藏匿隐蔽者之外,几乎全部惨遭屠戮。
“扬州烟爨四十八万户,至是遂空。
这便是骇人听闻,不容被历史抹杀的扬州十日。
扬州是大运河上非常重要的商业城市,是两淮盐运的中心,不仅汇聚天下财富,更是江东文脉所在。
但经过这短短的十余日,便被彻底的摧毁,往后数百年里,再也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样子。
但颇为黑色幽默的是,直到两百多年后,《扬州十日记》从日本重新传回中国,许多中国人才第一次知道,清兵入关时犯下的累累罪行。
许多新军将领,就是读了此书之后,才下定决心要推翻清朝的。
说回史可法,史阁部在守城上的种种错误,这时已经不忍再苛责了,他是很有气节的民族英雄,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决心以死明志,证明自己的忠诚。
除此之外,从决议拥立谁做新皇帝的严重失策开始,这一年多来,作为整个南明政权威望最为崇高的大臣,作为江北诸军的督师,史可法本应该有更大的作为,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但他除了临阵一死了之外,其他几乎全错,实在没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。
后世苏联解体之后,有人评价戈尔巴乔夫说,这是个将权力丢在地上让疯子去捡的懦夫。
史可法不能说是懦夫,但确实从来没有真正的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
就在局势危如累卵,几路大兵压境之时,江左君臣依旧为“大悲”“北来太子”和“童妃”这三大案闹得昏天暗地,不可开交。
所谓的大悲案,简单来说,就是有一个叫大悲的和尚,谎称是亲王,先说崇祯在时,封他为齐王,他不要,后来又改封他为吴王。
这是明显的胡说八道,稍有常识的人都能识破。
但最为吊诡的是,大悲和尚在受审的时候,居然说出“潞王恩施百姓,人人信服,该与他皇帝坐”这样的话。
潞王朱常?,神宗皇帝的侄子。也不知是怎么传出来的,说是素有贤名,当初崇祯自挂东南枝之后,南京诸臣,尤其是东林复社的那一伙人,非常热衷于拥立朱常?的方案。
史可法受到这种论调影响,起初也不同意拥立序更靠前的福王朱由崧,甚至还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说福王“贪、淫、酗酒、不孝、虐下、不读书、干预有司”,将这个素未谋面的小福王臭骂了一通。
结果,马士英转头就联合高杰、黄得功、刘良佐和守备太监韩赞周,宣布拥立朱由崧。
立刻使史可法陷入到了极大的被动当中,无言以对,无颜自立。
定策之功,就此落到了马士英和勋镇们的手中。
史可法的政治能力可见一斑。
尽管福王登基,但东林复社一系,始终对这位新皇上充满了攻击性。
这个所谓的大悲和尚,就是这帮人整出来的大活。
北来太子案和童妃案同样如此,都是在借题发挥,指桑骂槐,用来攻击和动摇朱由崧即位的合法性。
五月初五日,南都奉天门内,一众大佬、阁臣填塞其间,站得满满当当。
这时史可法遇难,扬州失陷的消息已经传来,不用看地图也都知道,扬州距此只有咫尺之遥了。
两百多年前,上一个打入南京的王爷,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进攻的。
局势如此,几乎人人脸上都有忧色。
“陛下,陛下,如今之计,惟有大江可以凭依。鞑子生长于苦寒之地,善弓马骑射而不善操舟,有虏伯郑鸿逵率水师游弋江上,想必鞑子只能望而兴叹,徒呼奈何!”兵部尚书阮大铖说着自己都不信的话。
但没办法,现在这个局面,只能寄希望于长江天险。
郑鸿逵是大海盗郑芝龙的弟弟,当年那都是叱咤东洋的风云人物,而清兵呢,是从辽东深山老林里钻出来的,再怎么说,也不是轻易就能渡过长江来的吧?
马士英也站了出来,慷慨陈词:“陛下,如今左军势重,日夜攻击江防,臣请速调兵马赴援!”
“不可!”刑部侍郎姚思孝道:“左军前为靖国公所阻,后又有闯逆追击,覆亡就在转瞬之间,此事可稍缓。但北兵侵略如火,情势危急,臣伏乞陛下,以御北为重,勿征调江北兵马。”
姚思孝这么一说,御史乔可聘、成友谦全都出言赞同。
就连朱由崧也频频点头。
朱由崧虽然昏聩,但他耳根子软,性格懦弱,是个听劝的啊,如果能有个诸葛亮那样总揽大局的有力之人,他也是能够安安心心当一个废物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