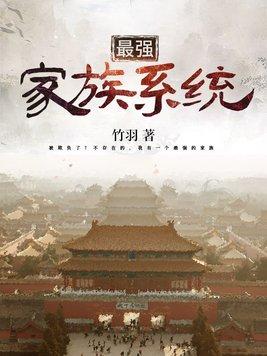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他是她的狗? > 第 64 章(第1页)
第 64 章(第1页)
姜雁抬头,线衫的帽檐遮住他的脸,下颌紧紧绷紧,他跑得突然,风将他碎发吹开,露出一点苍白的额角,还有额角上淤青的新伤痕。
陈、喣。
陌生的青年背对着众人,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。微微弓着身,将姜雁完全护在身下,肩背黑色的线衫被灼烧出焦痕,空气中烟熏火烛味混着潮湿散开。
一盆滚烫,四零八落。
他盯着她,甚至没发出一声闷哼,只是背部肌肉,砸得紧绷,上下仔细扫过,却只是微微皱眉,嘴角挤出弧度:“应该掀桌子才对,太温顺了,一点也不像姜雁。”
只是这句话,这是这个瞬间。
这么久的时间,这么郁闷难忍的场景,所有的包围讽刺、委屈从胸口蔓延,一点点爬上少女那双渐渐泛红的眼,她偏过眸子将一切吞下。
灵堂鸦雀无声,所有人出乎意料般看向这个的陌生的、年轻男人,只见他缓缓站直,动作有些停滞,毕竟被砸的那一下并不轻松。他没有先清理背后的狼藉,而是站定,任由那些灰掉落,挡在她面前。
转身。
帽檐下那张脸才露出,冷白皮、鼻梁高挑,嘴唇的弧度抿成一条线。脸上没太多表情,只有双珀色畜了些戾气的眼睛。
“灵堂。”他开口,声音不高不低,扫过姜家的人:“正是划分利益的好地方。”
陈喣的目光锁定的姜母,说着嘴角浮起温意的假笑,眼畜了冷意,那老太太被看得发毛。
“老太太。”他的语气甚至更礼貌了些:“刚才的火,是烧给你儿子的,还是孙女的?”
老太太不懂文化,只恨这个拖油瓶,现在儿子死了想着那些钱,嘴巴哆嗦着想说什么,却被陈喣抬手的虚势给挡了回去。
“不着急。”他视线扫过每个面色不善的姜家亲戚:“要分东西,也得先吃饭,来送奠金的人不会连口饭都不给吃吧。”
他从口袋拿了份白包。
姜家人眼看着灵堂门口围起一圈的看热闹的,只好吞下这口气,冷哼着抽了陈喣的奠金,朝屋外午席坐下。
人走了。
灵堂又恢复安静,香烛燃烧噼啪,门口宴席的小声指点,老钟叹了口气,跟着出门,房间只剩两人。
这时候,陈喣才将视线落回她身上,她一直跪坐在硬碎草包上,依旧保持着低着头的姿势,能看见乌黑的发顶和一小块苍白后颈。
陈喣在她面前蹲下。没拉她,只轻轻抚开她肩上的纸灰,她侧脸垂眸,脸颊触碰到他冰凉指尖,两人都不可察颤了下。
“地上冷。”他说,声音很低。
她没动,只是看着地上扭曲灰烬。
陈喣也没催,只是这样蹲在她面前,好几秒,她才抬头,四目相对,她强忍着、倔强着忍着,然后,对他伸出的手摇摇头。
拒绝了陈喣的搀扶,她自己可以站起来。
撑着冰冷的地板,起身,没有拍打身上的灰烬,而是将垂到眼前的碎发别到耳后,重新挺直了脊梁。
她可以的。
姜雁绕到冰棺后,从侧门走了出去,陈喣追了上去,到了门口人却不见,陈喣顺着侧门到绕到柏树前,中午太阳大,这里却阴冷看不见人。
他正要转身去别处找时,姜雁端了两碗面身后,抬起头,盯了他一会,蹙眉:“又伤了。”
风冷,也大。
吹起陈喣的帽檐,那块额角新鲜、带着淤青的皮肤在他脸上格外刺眼,她看着,他下意识想挡,手抬一半却绑了绷带,只好放下,偏了偏头。
“又伤了。”她重复一遍。端着面,站在原地。
陈喣扯扯嘴角,想做个无所谓表情:“小伤。”
她没接话,将其中一碗递给他:“吃吧。”率先走到柏树下一块花坛台阶坐下。陈喣跟上去,在她旁边半步元的地方并排坐下,沉默吃着。
陵园大锅煮的面,清汤寡水,没味道,可两人吃的认真,吃到一半的陈喣才开口:“我建议,你还是保住房子,他们势必什么都想要,马上高考,你没时间跟他们耗官司,但让步太多,他们会觉得你好拿捏,以后麻烦不断。”
姜雁停下筷子,转头看他。
陈喣顿了顿,继续说:“房子是你想要的,那有你跟……的记忆,最快的办法就是是用钱买清静。不是分赔偿金,是额外一笔,算‘买断费’,让他们签字画押,以后两清。”
姜雁还是盯着他,平静坦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