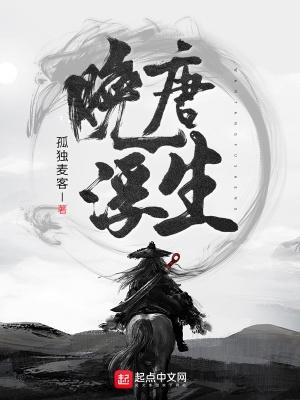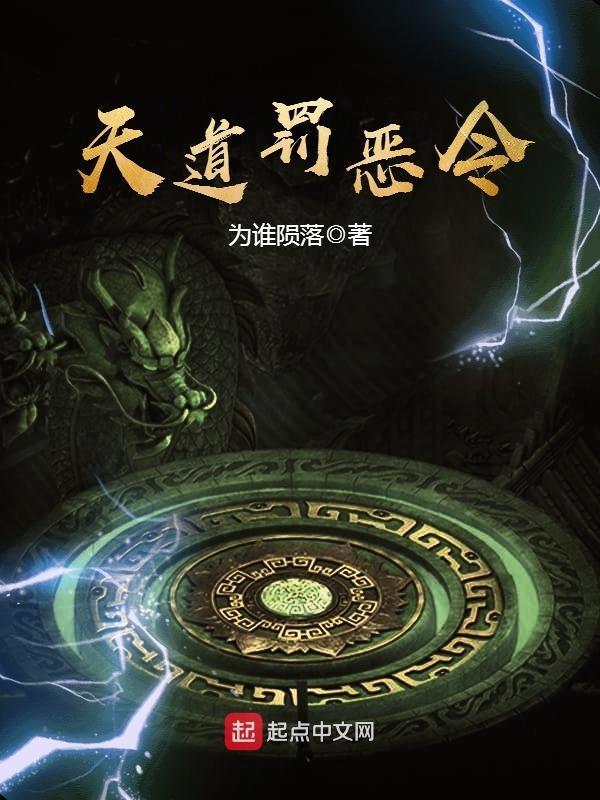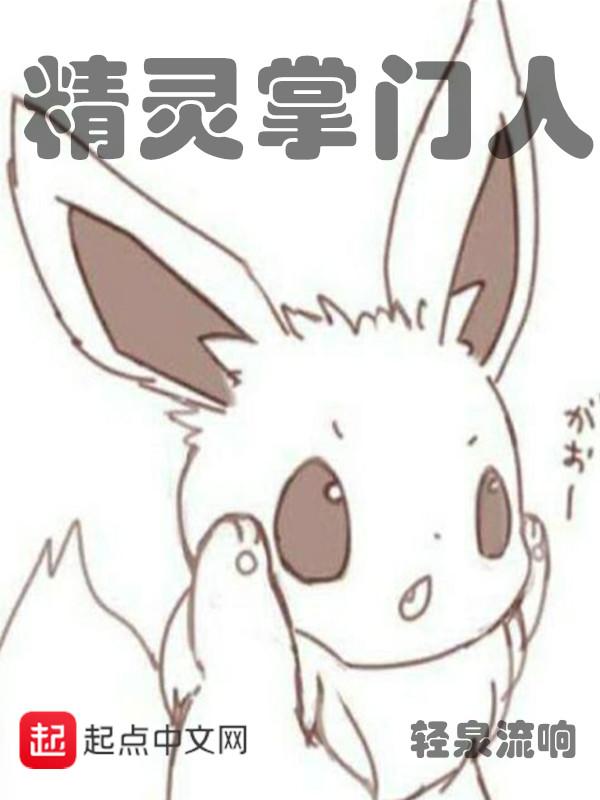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刚准备高考,离婚逆袭系统来了 > 第697章 被抓包了(第1页)
第697章 被抓包了(第1页)
从景府小区离开,江年回到了学校。正好趁着教室没人,写了一张卷子。
高三写习惯了,写起来只觉丝滑。
不过,张柠枝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。声音清脆,语气中带着一丝惊喜。
“你现在在哪呀?”。。。
夜深了,北京的风穿过政法大学检察学院的宿舍楼,带着北方特有的干燥与清冷。江年坐在书桌前,台灯的光晕笼罩着那页课题申请书,纸上的字迹工整而坚定,像他此刻的心境。窗外偶尔传来几声虫鸣,远处操场上有学生夜跑的脚步声,一切安静得近乎庄严。
他没有睡意。
手机屏幕亮起,是南城志愿者团队的群消息。张强发了一张照片:他家院子里,两个孩子正蹲在小黑板前写字,稚嫩的手握着铅笔,一笔一划写着“正义”二字。配文只有短短一句:“江年哥哥,我教他们认这两个字。”
江年的嘴角微微扬起,指尖在屏幕上停顿片刻,回了个“好”。
他知道,有些东西正在悄然生长。不是靠一场胜利、一次翻案,而是靠无数个微小的坚持,在人心深处扎下根来。
第二天清晨,阳光洒进教室时,他已经站在讲台上,作为新生代表发言。台下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,有保送的竞赛冠军,有高考状元,也有像他这样因特殊贡献被破格录取的学生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竞争气息,仿佛每个人都在无声地宣告:我是最值得这个位置的人。
江年没有穿西装,只是一件简单的白衬衫,袖口挽到手肘,露出结实的小臂。他不看稿子,目光扫过全场。
“我曾经以为,正义是可以用分数换来的。”他说,“高三那年,我以为只要考出750分,就能让父亲的名字重回警局荣誉墙;我以为只要写好那篇关于‘光’的作文,就能唤醒人们对真相的记忆。”
台下一片寂静。
“后来我发现,真正的正义,从来不在试卷上,也不在新闻头条里。它藏在母亲缝补警服时颤抖的手指间,藏在王建国老师烧给林婉清的那一叠底片灰烬中,藏在张强跪在化工厂门前磕下的三个响头里。”
他的声音不高,却像锤子敲在铁板上,一声声砸进每个人的耳朵。
“我们学法律,不是为了成为体制里的螺丝钉,更不是为了将来穿上制服去审判别人。我们学法律,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有人不敢说话,还有人说了真话却被关进监狱八年,还有人为了保护证据,宁愿二十年不开口。”
他顿了顿,目光落在后排一位戴眼镜的女生脸上??那是李清容推荐给他的同班同学,曾在高中组织反校园暴力社团。
“我希望四年之后,当我们走出这所学校,别人提起我们的名字,不会说‘这是个高材生’,而是说‘这是个敢为弱者发声的人’。”
掌声如潮水般涌起。
课后,辅导员找他谈话。
“你说得很好,但也要注意分寸。”她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,“你是公众人物,一句话可能引发舆论风暴。学院希望你能稳重些,先完成学业,再谈理想。”
江年点头:“我明白。但我不能假装看不见问题。”
“那你打算怎么做?”
“我想开一门选修课。”他说,“名字叫《被遗忘的案件》。邀请当年参与南城三案的亲历者来讲课??王建国老师、李清容检察官、吴师傅,甚至张强。让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们:司法不只是条文和程序,更是活生生的人。”
辅导员沉默良久,最终叹了口气:“我会向教学委员会提交申请。不过……你要想清楚,这些人身份复杂,有的曾背负污名,有的还在接受调查关联审查。这不是讲故事那么简单。”
“正因如此,才更有必要。”江年直视她的眼睛,“如果我们连讲述真相的人都不敢请,又怎么培养未来的检察官?”
离开办公室时,天已近午。他在食堂遇见周野。
这位昔日刑警如今调任公安部督察局,专责内部纪律审查。他穿着便衣,胡子拉碴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。
“听说你在搞事?”周野递来一瓶冰镇可乐,咧嘴一笑,“你导师李清容刚给我打电话,说你非要请我去做讲座,主题是‘一个警察如何从执行命令变成帮凶’?”
江年也笑了:“你不觉得这很有代表性吗?”
“代表什么?代表我们这群老家伙都是失败品?”周野摇头,“江年,我不是不想讲。可你知道现在多敏感吗?上面刚抓了几个‘两面人’,底下人人自危。我要是真把当年那些潜规则说出来,恐怕不止是我倒霉。”
“所以才需要有人开口。”江年压低声音,“你以为系统真的消失了吗?它只是换了壳子继续运转。陈昊倒了,刘振邦进去了,可那些默许他们作恶的机制还在。考核唯结果论、办案指标压力、上下级之间的‘默契’……这些才是真正的毒瘤。”
周野盯着他看了很久,忽然叹气:“你小子……比我当年狠。”
“我不是狠。”江年轻声道,“我只是不能再看着下一个‘江卫国’被埋进土里。”
两人并肩走在林荫道上,影子被拉得很长。
傍晚,江年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:
【我是林老师的学生,现在在西北支教。昨天看到你在北京演讲的视频,哭了。她说过,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人顺从,而是让人觉醒。谢谢你替她完成了这句话。】
他久久未动,回复了一句:
【请你代我向孩子们问好。如果可以,请带他们读一遍《少年中国说》。】
手机刚放下,李清容来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