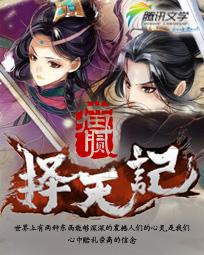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非正常美食文 > 第513章 云中食堂优秀员工的基本素养(第3页)
第513章 云中食堂优秀员工的基本素养(第3页)
中午,苏慧去了那所职高。她在公告栏贴上新的《家属证言》:
>致所有曾因父母职业而羞愧的学生:
>你不必为他们的身份道歉。
>真正可耻的,是这个逼你羞愧的世界。
>你的父亲或许满身油污,
>但他点亮的每一盏路灯,
>都曾照亮你回家的路。
她转身时,看见几个男生围在公告栏前,低声议论。其中一个摘下帽子,露出烫着“爹味”二字的短发??那是他们班最近流行的自嘲发型。
他走上前,把帽子递给苏慧:“能帮我写一句吗?我想让我爸知道……他的电工证,是我书包里最不敢掏出来,却又最舍不得扔的东西。”
苏慧接过帽子,在内衬绣上一行小字:
**你修的不只是电路,还有我断裂的勇气**
下午,社区礼堂再次开放。
“补真计划”第二场直播开始。林晚坐在台前,面前放着麦克风。她身后大屏播放着一段视频:是她过去某场直播的弹幕截图,满屏“心疼姐姐”“泪目”“打赏火箭”。
“这些眼泪,是为虚构的故事流的。”她说,“可真实的人,反而得不到一句‘我信你’。”
她点击播放另一段视频??是那位电工父亲在电线杆上工作的画面,风吹得他摇晃,安全绳勒进肩膀。
“这才是真实的苦难。”她声音坚定,“它不戏剧,不煽情,但它每一天都在发生。”
她宣布:“今晚起,我的直播间不再讲虚构故事。我要做一件事??帮普通人录制‘真实语音日记’。你可以匿名,可以说半句,可以哭,可以中断。只要你愿意开口,我就替你播出去。”
台下有人举手:“我能录吗?我想告诉我妈,我不是懒,是得了抑郁症。”
另一个声音响起:“我也想。我想说,我不是不孝,是我爸喝酒打人,我不得不搬走。”
林小满坐在角落,听着,记着。结束后,他递给林晚一张新纸条:
>真实不需要完美,只需要出口。
>从今往后,你的每一场直播,
>都是一口锅,熬着那些被冷落的话。
她握紧纸条,仿佛握住一根救命的绳。
同一时间,林溪的新作文在学校论坛爆了。评论区最初是嘲讽:“装穷博关注”“又是留守儿童剧本”。可渐渐地,有人开始回应:
>“我也是便利店孩子的子女,我爸值夜班十年,我从没见过他周末陪我看电影。”
>“原来不是我一个人,早餐永远是冷掉的包子。”
>“谢谢你写了我们不敢说的话。”
一位老师留言:“我教了二十年书,第一次意识到,所谓‘不合群’的孩子,可能只是家里没饭吃。”
傍晚,铜锅第三次滴水。
水珠落地,拼出四个字:
**你被看见了**
林小满蹲下,用手轻轻描摹那四个字。他知道,这不是魔法,是累积??是每一个敢于袒露脆弱的人,用伤口划出的痕迹。
几天后,陈婉的第二堂课开讲。主题是《羞耻的重量》。
第一位学员是个女警官。她说:“我抓过小偷、处理过家暴,可我从来没告诉别人,我父亲是性侵犯。他毁了一个女孩的人生,也毁了我们的家。我妈带着我和妹妹逃了三次,最后一次,他拿着刀追到桥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