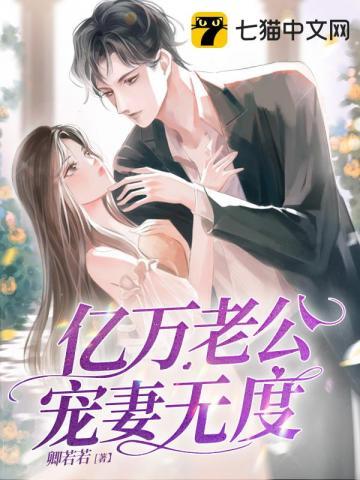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三国:王业不偏安 > 第283章 故人之姿(第2页)
第283章 故人之姿(第2页)
刘禅眉头一皱,想到了什么,于是率霍弋、诸葛乔、法邈、张绍等随侍文臣来到江畔。
不多时,一艘轻舟在汉军战船护送下驶近码头。
几名虎贲郎上前,将十余来人引至一身常服的刘禅面前。
那为首的老者被引至刘禅一行人身前,但见一年轻小将长近八尺,气宇不凡,又被众人簇拥,心知是主事之人,连忙上前,躬身行礼:
“几位将军,草民乃荆门丹阳聚文氏之长,姓文,名正。”
说着,他双手递上一封崭新的帛书拜帖,起身时,目光在刘禅脸上停留片刻,微微一怔。
刘禅接过拜帖,快速浏览。
上面详细记述了文氏在吕蒙白衣渡江、关羽败走后,他们文氏曾如何暗中帮助过流散的汉军将士。
又夷陵之战时,他们如何向前来讨伐东吴的先帝进献了粮草万石。
最后又写到,他们文氏在孙权占据荆州后,如何受到孙氏麾下官吏的盘剥和打压云云。
当然,拜帖所书最后面,也是最重要的是,他们文氏此番携粮三万余石前来进献。
“文老。”刘禅将拜帖递给身后的诸葛乔,不动声色地问,“我大汉王师初至夷陵,胜负犹未可知,而吴贼已近在眼前,此时送来粮草三万余石,不怕万一我大汉失利,孙权秋后算账,累及宗族吗?”
“将军明鉴。”那文正正色道。
“大汉陛下去岁亲征北伐,克复关中,还都长安,威震天下,天下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
“至于去岁秋,大汉陛下又于西城破吴,那为孙权镇压夷陵数载的步骘,也在陛下手中败而成擒。
“荆州士民思汉久矣,思先帝久矣,思丞相久矣,于是无不振奋,本以为巫县在吴人手中有金汤之固,汉之伐吴或将点到为止。
“不意大汉王师竟突破吴人设于巫县、秭归固若金汤的江防,进围夷陵,逼得朱然坚壁清野,不是天兵又是什么?如此雷霆之势,岂非天命重归于汉?
“老朽居于夷陵之野,受迫于孙氏豺狼之吻,无幸沐汉圣恩,然生是汉人,死是汉人,闻汉一再破吴,知荆州之仇必报,夷陵之恨将雪,是以纠合文氏,愿举族相助,为大汉王业略尽绵薄!”
刘禅闻此默然,又有些振奋。
眼前这文姓老者说得实在,而他对大汉的态度与看法,基本上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荆州豪强对大汉的态度与看法。
所以说,战争的胜利,确实比任何口头或文字的舆论宣传都要有用得多,战争胜利的本身,就是最好的舆论宣传。
荆州人心可用。
“不知将军可是国姓?”那文氏老者见身前这位蓄着一副短须的年轻将军沉默,忽然问道。
“哦?”刘禅一滞,“我确姓刘,文老如何能知?”
那文正回忆道:“老朽观将军年轻英武,气度非凡,像极了……像极了六年前,在此地接见过老朽的一位将军。”
刘禅闻此一怔,心中了然,旋即接过话题道:“老先生好意,我代大汉将士领受。这三万石粮食,确可解我王师燃眉之急。此事,我必会如实禀报陛下。”
文正闻言,面上顿露喜色,心中大石落了一半:
“多谢将军!待王师克复夷陵,重振荆州之日,还请将军务必光临丹阳聚,让我文氏略尽地主之谊,以报今日引荐之恩!”
区区一个荆门文氏,一个小地方的小豪强,名不见经传,想要献美于汉,那也得看大汉愿不愿意收,更得看眼前这位主事的将军,愿不愿意把他的话传给上面的大人物。
不然话说得再好听,上面的人听不到有什么用?
献的粮再多,上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,又或者三万余石粮草最后报上去的只有一万石,那又是怎么个说法?
所以说,此言既表感激,也隐晦地希望这位刘姓将军能在大人物面前多为文氏美言几句了。
就在这时,文正身后那位年纪稍轻的老者上前一步,目光却越过了刘禅,直接落在他身后的霍弋身上,语气带着几分激动和不确定:
“敢问这位少君,可识得南郡枝江的霍峻霍仲邈?”
霍弋闻言,神色微微一滞,而后先是看向刘禅,得到默许后,才跨前一步,拱手沉声道:
“小子霍弋,字绍先。
“乡老所言,正是先父名讳!”
那老者闻此顿时眼前一亮,仔细地上下打量霍弋,最后声色既感慨又激动:
“原是仲邈之子!难怪有伯信、仲邈兄弟之姿!绍先,绍先,绍先人烈志,好字,好字啊。”
刘禅与霍弋、诸葛乔等人交换了一个眼神,显然有些意外,细想却又并不意外。